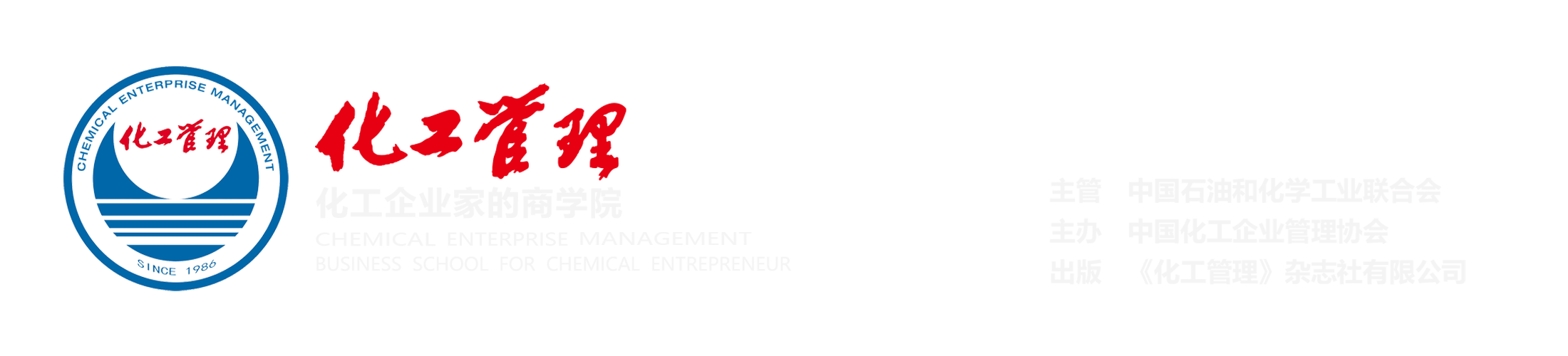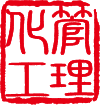编者按:2021年8月9日,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正式发布,该报告再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以及全球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研究员早年曾担任IPCC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高级经济学家,多年致力于能源与气候政策、可持续发展等的研究,对低碳经济、零碳经济有着深入的认识和见解。本刊第4期刊发了潘家华研究员《中国碳中和的时间进程与战略路径分析》一文,文章指出中国实现碳中和,必须要求化石能源消费清零,其中煤炭在2055年“基本”退出,石油在2058年前后可以“大略”清零,天然气在2059年前后“大体”退出。技术选择基本是电力替代,少许的生物质能替代,少许的二氧化碳碳捕集与埋存技术。文章强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既需要颠覆性技术革命,也需要系统性社会变革。
作 者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
刊 期 《财经智库》2021年第4期
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和国际合作进程中,不断深化和聚焦碳中和。2015年《巴黎协定》的正式签订,确定了到21世纪末相对于工业革命前全球温升不超过2℃,并努力争取控制在1.5℃的减排目标,这更加迫切要求各缔约方提振雄心,强化减排行动。2018年,IPCC发布《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明确指出实现1.5℃的温控目标需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全球二氧化碳净零排放。为此,全球应致力于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力争于本世纪中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即使有少许排放,也可以通过人为的工程措施和生态系统吸收而达到全球碳排放归零的动态平衡,以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大力推进碳中和的目标进程,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能源服务,碳并非是必需品。化石能源是额外于气候系统的碳源,碳中和所需要的,就是要将额外于气候系统的化石能源碳清零。实现碳中和,依靠改进型的技术创新是不够的,一方面需要颠覆性的硬技术革命,以彻底取代并告别高碳的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这是碳中和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还需要社会性的软技术变革,从而加速并保障碳中和的实现进程。本文首先对碳中和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重点对国际碳中和发展的背景、进程以及中国碳中和的目标刚性等做相关梳理,提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战略路径和技术选择,以期为更好地推进碳中和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碳的来源及分类
碳从何来,减什么碳?20世纪80年代的温室效应关注的重点是二氧化碳。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UNFCCC)中,并没有明确列出温室气体的种类。90年代初期,气候变化经济学模型参数以化石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作为指标,几乎没有纳入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专司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早期的报告中,所侧重的也是化石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对于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科学评估的内容较为有限。1997 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次明确了 6种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和三种含氟气体,2012 年又增加了一种含氟气体。90 年代后期,自然生态系统碳排放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受到关注,被纳入评估内容。
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有三大类主要来源。一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过程中释放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和甲烷。第二类则是生态系统中绿色植物和以绿色植物为食物或能量来源的动物在生命周期中所释放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第三类则是工业生产过程释放的和人工生产制造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各种含氟气体,包括各种制冷剂、发泡剂。温室气体排放的构成中,二氧化碳占78%左右,甲烷占17%左右,氧化亚氮占3%,含氟气体占2%。相对说来,非二氧化碳占比相对较小,而且大略稳定,增速和增幅均较为有限。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温室气体排放增速和增幅的来源,主要是化石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见图1、图2)。
注:2020年为预测数据。
资料来源:Friedlingstein 等(2020)。
资料来源:Grant等(2021)。
(二)温室气体的属性
温室气体的属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气候中性碳,主要是自然生态系统各种生命过程和土壤中的碳循环。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形成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再通过枯枝落叶、死亡和动物食用而转化、排泄,生命有机体中的碳又回到大气。自然碳循环大致是平衡的,某一个时间段、某一个地区,可能有盈或亏,但总体上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原则上是中性的。另一类则为气候灾性碳,主要源自于化石能源相关的排放和人工生产制造的温室气体。之所以说这类碳具有气候灾性,主要是因为这些碳是额外于气候系统的。也就是说,原本大气中并不存在,是人为制造或者是地质年代形成于地下,通过现代工业手段挖掘出来并释放到大气中的,这部分碳提升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引发地表增温,造成气候灾变。尽管含氟气体全球增温潜势高,但总体数量少。因此,气候灾性碳的重点在于化石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三)碳中和的基本内涵
所谓碳中和,实际上就是净零碳排放,指的是目标时间节点及之后的流量动态清零。通常承诺的是目标年及其以后的碳排放流量动态清零,而非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存量归零。也就是说,碳的排放源与碳的清除量的动态平衡。需要明确的是,气候中性碳既是碳源(排放),也是碳汇(吸收),而且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碳循环变化,在测度统计上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通常误差高达50%;气候灾性碳是额外的,统计误差较小,多在5%以内。非二氧化碳气体在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比不高,且甲烷也有40%源自于化石能源的开采、运输和使用。因而,化石能源碳就成为碳中和的首要或第一目标。尽管世界上有各种温室气体的统计和监测数据,但统计最为及时、最为精准的,是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见图2)。实现碳中和,从措施上可以多管齐下,包括农业、林业、含氟气体,但各国碳中和的抓手和目标指向,原则上仍然是化石能源相关的碳排放。
世界各国达成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共识,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认知深化和政治共识过程。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但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都表明,全球变暖趋势在持续。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表明,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1 ℃,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个暖年,2015—2019年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五个年份。地表升温,冰川融化,雪线退缩,冻土层解冻,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消失,极端气候事件增多。1961—2019年,中国年平均地表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2019年,中国平均地表温度较常年值偏高1.4℃,为1961年以来的最高值(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2020)。全球增温而引发的极端气候事件,频次增加,强度增大。当然,化石能源开采、燃烧和炼化对于生态的破坏和大气环境的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有着持久、有害的影响。此外,在有限的地球空间,化石能源不可能是无限的,300年工业化进程已经耗尽许多地方的化石能源储量,人类还要在地球上延续百万年、千万年,乃至上亿年,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不可能支撑人类未来的长远发展。因此,碳中和不仅仅是为了减排,更是为了地球未来,人类未来。
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是自然和人类干扰双重因子作用的结果,人类从认识温室效应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再到明确碳中和,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政治博弈过程,从而不断明晰聚焦净零碳。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温室气体减排并没有相关条款规定,而且对温室气体也没有明确的界定。1997年达成发达国家总量减限排的《京都议定书》,明确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下,发达国家即附件I国家在2010年相对于1990年整体上减排不低于5%,实际上谈判结果为5.2%,但由于美国拒绝批准,直到8年后的2005年才生效实施。之后由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相继退出,《京都议定书》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是,该议定书具有巨大的积极效用:给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即碳排放是要受到限制的;发达国家出资在发展中国家减排而获取减排额度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启了发展中国家低碳发展的序幕。
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从科学上明确2℃温升的阈值。2007年12月联合国巴厘岛气候会议上,欧盟第一次明确2℃温升目标,并得到多数国家的接受和认同。2009年谈判达成但最终没有取得共识的《哥本哈根气候协议》,第一次在国际法律文件上确立2℃温升目标,虽然没有细化具体的零碳指标,但规定附件I、非附件I缔约方自主承诺。2015年,在中美等国政治家的强力推动下,联合国气候会议达成《巴黎协定》,不仅重申2℃温升目标,而且进一步寻求争取1.5℃温升目标的可能,并将温升目标转换为碳排放控制目标,明确在21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发展中国家排放尽早碳达峰,所有国家提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定期在全球盘查减排进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授权下,IPCC于2018年完成《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强化了1.5℃的科学事实和属性。有的国家,例如瑞典,早在2017年就通过立法明确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多数欧盟国家在2019年宣布2050年碳中和目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向世界宣布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后,2021年4月拜登政府承诺在2035年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实现无碳电力,2050年实现碳中和(见表1)。
资料来源: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349401。
碳中和是目标导向的刚性约束进程,一旦承诺碳中和目标,碳排放达峰就成为从属性的安排了(潘家华,2020)。这是因为,碳中和的目标刚性和时间规定性,要求在206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如果峰值越低,则清零碳排放的阻力就越小,难度相对较轻;如果攀高或推后碳排放峰值,意味着将会有更多、更高的碳锁定,要么资产浪费,要么碳中和时间节点后移(潘家华,2020)。工业革命的成功源于煤炭动力,工业化进程的动力依然是化石能源。而煤电、煤化工、石油开采、炼化,均属于高度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动辄数十亿元,乃至于数百亿元,经济运行期多为30年甚至更长(潘家华,2021)。如果现在投资,2025年投产,35年则要到2060年。如果中间有什么变故或碳中和提速,现在的投资就需要提前退出,以免造成资产浪费。因而,当前化石能源100亿吨的碳排放要在2060年前大略清零,不可能等到最后一秒钟,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实现化石能源开采、使用的排放逐步归零。
表2给出了中国实现《巴黎协定》控制2℃温升目标和1.5℃温升目标的减排时间表。显然,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绝对主体,非二氧化碳排放,尤其是甲烷,原则上也应该有40%左右的排放归入化石能源。因而,在相当程度上讲,化石能源消费的清零过程就是碳中和的时间进程。
注:CCS(Carbon Capture & Storage)是指碳捕集与埋存; BECCS(Bio-Energy Carbon Capture & Storage)是指生物质能源碳捕集与埋存。
资料来源:2020年、2030年、2050年数据源自项目综合报告编写组(2020)中1.5℃情景;2060年数据系作者根据碳中和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分析研判所得。
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碳中和目标实现时间是2060年前。从字面上理解,时间刚性可以解读为最晚必须在2059年,一般不会也不可能早于2051年。既然是碳中和,也就意味着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必须大体清零,但不一定是100%归零。尽管CCS的成本高,大规模利用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为保障能源系统安全,也有可能小规模利用。同样,森林碳汇是气候中性碳,但在经过数百年的系统性森林生态系统破坏后,森林碳汇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可能实现每年一定量的碳吸收。工业过程碳排放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尽管量不大,占比不高,但在最后的碳中和测度和核查中,也有较小数量的存在。因而,碳中和的重点和难点,只能是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
如果聚焦于气候灾性碳,也就是化石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包括甲烷和氧化亚氮),减排顺序依次如下。
首先是煤炭。同样热值的能源服务,煤炭的碳排放因子最高,每吨标煤热值的煤炭大约排放2.6吨二氧化碳。考虑到其他化石能源相对低碳,煤炭退出时间顺序应排第一。发达国家多在2035年前退出煤炭。考虑到我国许多超超临界百万千瓦级别的煤电投产时间可能晚至2025年,经济运行期(投资回收期)为30年,退出时间最晚需要在2055年。煤电的缺口,将全部由零碳的可再生能源和储能补足。在2045年前,钢铁以外的固态煤炭使用全部退出。2050年前后,由于钢材存量大幅提升,废钢短流程电炉将占据主导地位,而依靠铁矿石的炼钢长流程所需的焦炭会被氢能取代,所需煤炭随着电炉的大量使用而退出。此时,退出的不仅是煤电,也包括煤制气、煤制油、煤制甲醇等煤化工项目。煤炭退出,则与煤炭相关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基本清零。
其次是石油。同样热值的能源服务,石油的碳排放因子大约为每吨标煤热值的原油排放2.1吨二氧化碳。石油产品多用于机动车动力,部分为化工原料,例如塑料、化纤等。鉴于纯电动汽车技术基本成熟,我国规划在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汽车市场的主流,多数国家也宣布在2035年禁止燃油汽车上市,我国大略可望在2040年实现禁止燃油新车进入市场。燃油汽车的使用寿命大约15年。这样,除航空以外的交通用油,有望在2055年全部为零碳电能所替代。2058年前后,航空用油可以为氢能、生物柴油或电能等所替代,从而实现燃油的大致清零。塑料、化纤等石油化工产品,在使用期内不会造成排放,但最终处理仍然会通过燃烧排放二氧化碳。因而,各种化纤、塑料制品,需要代之以金属、木材和植物纤维,可望在2058年以前逐步被取而代之。这样,石油开采、炼化、燃烧相关的二氧化碳、甲烷(油田伴生气)在2058年前后可以大略清零。尽管如此,社会上仍然会残留以石油为原材料的塑料、化学纤维等,需要较长时间彻底消除。
最后是天然气以及页岩气。每吨标煤热值天然气的排放系数为1.6吨二氧化碳,在化石能源中碳排放因子最低。天然气能源品位高,储藏运输方便,其他污染物含量少。也因为这样,英国、美国的减排主要就是得益于天然气和页岩气替代煤炭。在煤炭石油全面退出后,天然气大体在2059年前后退出。此时的大体退出,含义是仍然有少许用以支撑社会经济的平稳安全运行。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描述的化石能源碳的减排进程,第一是紧约束。不论是煤炭、石油还是天然气,基本上要在2055年以后才能大体退出。考虑到大型煤炭、石油开采、炼化项目的经济运行寿命,大略归零的时间需要在2059年,以满足2060年前的时间刚性。第二,化石能源退出,煤炭使用的表述是“基本”,应该几乎是100%,残存大略0.3亿吨,排放0.8亿吨二氧化碳;石油使用的是“大略”,有望达到95%,可能残存0.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大约为1.1亿吨;天然气使用的是“大体”,可能只有85%左右,大略残存1亿吨,排放二氧化碳1.6亿吨。因此,即使到2059年,化石能源碳排放仍可能在3.5亿吨左右。第三,技术选择基本是电力替代,少许的生物质能替代,少许的碳捕集与埋存技术。没有考虑采用大规模的大气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原因不仅在于成本居高不下,不具备市场竞争力,更因为这样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终端技术,只能消耗更多的资源,带来更大的风险。第四,2059年尚存的3.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可采用碳捕集与埋存技术大约有1亿吨,生物质能负排放技术BECCS大约有0.5亿吨,生态系统碳汇大约有2.0亿吨。这样,化石能源碳排放可大略清零。第五,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含氟温室气体、农业源甲烷氧化亚氮,大略每年在2.3亿吨左右,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可大略中和这一部分的人为排放。这样,森林吸收、生态系统碳汇需维系每年4.3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从而在2059年大体实现碳中和。
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9.8亿吨标煤,其中,零碳可再生能源占比15.2%,大约相当于7.6亿吨标煤。2030年,一般预测能源消费总量还会增加,有可能达到60亿吨标煤。之后,随着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能源效率不断提高,人口数量有所下降,参照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我国最终能源消费需求也可能出现负增长,能源消费开始呈现下降态势,到2060年,能源消费总量大略降至55亿吨标煤。其中,化石能源消费总量为1.8亿吨标煤,占比3.3%,二氧化碳排放大约3.5亿吨,相对于2020年减排96.5%,通过CCS和碳汇,最终排放基本可以清零。
从这一目标刚性倒逼的时间进程看,中国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从2020年的100亿吨,经过大约40年时间,到2060年减至3.5亿吨,减排率达到96.5%。相比之下,德国的碳中和进程从1990年的12.51亿吨二氧化碳,经过60年,到2050年减至0.62亿吨,减排率95.0%。从绝对量上看,中国的碳排放量比德国高出8倍,可见,中国的减排幅度、力度、难度均远超德国。
中国排放总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比重超过1/4,人均排放量也已超过欧盟的人均水平。项目综合报告编写组(2020)指出,中国2020年的排放在总量上已然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就是发达国家俱乐部全体成员的排放总量。
虽然实现碳中和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但是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的经验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表3展示的是德国研究机构关于德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德国碳中和时间进程是从1990—2050年,实际上,德国的排放峰值大约在1980年就实现了。因此,德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跨度是70年;第二,德国的碳中和并非是绝对清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刚性的排放需求,大约5%左右,需要采用额外的碳移除措施,例如碳汇或CCS;第三,从路径上看,能源替代的部分(能源、交通和工业),应该在2/3以上,通过能效提升即减少能源消费需求的部分不足1/3;第四,能源、工业、建筑和废弃物等领域的减排多出现在早期,而交通领域的减排较为靠后。这也就意味着,在没有颠覆性技术之前,交通领域实现能源替代是存在难度的,但随着纯电动汽车经济性的提升,交通领域的能源替代也就顺理成章了;第五,从减排的时间进程看,前30年减排约占1/3,后30年减排占比达到2/3。这意味着减排不可能高歌猛进、一蹴而就,需要长远谋划,从现实做起。
资料来源:根据Prognos等(2020)数据,作者测算所得。
德国碳达峰实现得较早,碳中和缓冲期较为充裕。但对于美国来说,其能源消费一直处于高位水平,而且由于与欧洲人生活方式的差异,其人均排放超过欧盟的一半,二氧化碳排放轨迹也表现出较长时间的高位平台期,峰值迟至2005年前后才出现,化石能源消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峰值大约为59亿吨,目前已经低于50亿吨(BP,2020)。美国需从2005年开始(或目前的50亿吨),45年时间减59亿吨(或30年时间减50亿吨)。从中美碳中和的实现路径来看(见表4):第一,美国早已达峰,目前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2030年的目标是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减少一半,而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第二,如果从现在起步,中国的减排总量超过美国的1倍,时间却只滞后10年,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城市化水平,远远不具备美国的优势,滞后时间远不只10年;第三,美国的技术和脱碳进程领先于中国,值得中国借鉴;第四,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和规模,要领先于美国,中国规划在2030年风光装机超过12亿千瓦,几乎是美国当前发电装机的总和,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走向碳中和,有难度,但也有优势。
注:*为拜登2020年竞选政策主张。
资料来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数据为2019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数据库;习近平主席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的发言、2020年12月12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美国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美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
前文中的时间进程和重点聚焦表明,中国要实现碳中和,必须要求化石能源消费清零,而首先要归零的是煤炭。我国的资源禀赋是多煤少油缺气,煤炭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占据绝对高的比重。21世纪初,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的比例超过70%。2010年之后,随着油气进口规模的扩大和大气污染管控的趋严,202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降至56.8%。即便如此,发达国家在2030年前后就能实现去煤,而我国即使是在2055年彻底去煤,煤炭占比每年至少也要减少1.5个百分点。相比美国和欧盟的化石能源排放源结构(见表5),中国的化石能源排放超过美国1倍,相当于欧盟的4倍,但煤炭的排放却相当于美国的7倍,欧盟的12倍。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但需要归零的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和高碳的煤炭,却高出发达国家1倍乃至10倍以上。
资料来源:Friedlingstein等(2020)。
既然碳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那么,彻底去碳,社会福祉水平也就不会受到影响。碳排放之所以伴生于化石能源,是因为我们需要能源服务,如果能源服务能够无碳化,自然地,化石能源碳排放也就消失了。这就需要颠覆性技术,而不仅仅是依靠提高能效。例如以煤炭为燃料的火力发电,从亚临界技术到超超临界技术,每度电的煤耗也从400克减少到270克。进一步提高效率,必然会进一步低碳,但绝对不可能零碳。如果能源服务不需要化石能源的燃烧,自然就没有碳排放了,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必须具有市场竞争优势。为什么世界各国在20世纪所有的努力,只能做到低碳,但到了2015年以后,各国才陆续提出碳中和?就是因为当时零碳电力价格太高,不可能完全取代化石能源。
注:2000—2020年的数据为各类发电技术装机的投资成本,2030—2050年数据为预测值(以欧美装机数据为基础的均值,不计财务成本,按2020年美元计价)。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能源小数据(ESmall Data)整理。
表6的数据显示,目前风能、太阳能、水能发电装机成本已经低于煤电。2000年,光伏发电每千瓦的装机成本是煤电的4倍。10年之后的2010年,光伏装机成本有所降低,但仍超过煤电的1倍之多。到了2020年,光伏装机成本已降至煤电的40%。预计到2050年,光伏装机成本只有煤电的20%;如果煤电通过CCS脱碳,光伏成本将不足煤电的1/10。风光发电具有间歇性特征,需要储能,但水电、生物质电力与煤电一样,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而且抽水蓄能成本低、效果好。天然气具有成本优势,碳密度也相对较低,但仍然有碳排放,在碳中和时代,不允许大规模使用天然气发电。核电作为迈向碳中和的过渡性能源,可以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其风险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因此,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明确去核,并没有将核电纳入碳中和的主要技术选项。中国目前拥有一定的核电装机,但从长远看,在可再生能源经济性和安全性已经可以满足经济社会能源需求的情况下,也并不适合纳入碳中和的技术选择。
在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应用方面,后来者可以居上。2000年前后,中国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概念在媒体和技术研究中均较为少见。到2010年前后,中国的风、光电力设备的生产、安装和使用,才真正起步。之后,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从微不足道到独领风骚,只用了10年多时间。中国电力大数据显示(见图3),2011—2020年,中国的光伏装机从212万千瓦猛增到2亿5千多千瓦,增加了119倍!其间,光伏上网电价补贴从每度电2元到2018年后的平价上网,市场竞争力超过煤电。中国的光伏组件在世界上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以至于欧美发达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干扰国际市场交易,动用“双反”手段打压中国产品。
资料来源:中国电力联合会(2021)。
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亿千瓦以上,显然超过了国际社会的预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年,中国的风光电力新增装机超过1.2亿千瓦,装机总容量超过5.3亿千瓦。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如果将未进入电网的分布式装机纳入,2030年可望达到20亿千瓦。2020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占世界总量的35%,是美国的2.5倍(IRENA,2021a),印度的11倍。
实现碳中和,不仅是电力生产侧的零碳革命,也必须要求能源消费侧的颠覆性技术革命。汽车是石油革命的产物,是石油产品终端消费的主体。碳中和意味着改进型技术的彻底退出,颠覆性技术的全面替代。纯电动汽车或其他形式的新能源汽车,全面取代碳基燃料的燃油汽车,是碳中和终端消费或需求侧的不二途径(IRENA,2021b)。如果燃油汽车不能被颠覆,则石油消费和炼化的排放,将因为社会的需求刚性不可能清零。汽车燃油效率无论怎么提高,都只能低碳,不可能实现零碳。而纯电动汽车不需要燃油或燃气,只要电力源自于可再生能源,就可以驱动。从某种程度来说,纯电动汽车也可以是间歇性风电、光伏发电的储能设施。在纯电动汽车领域,中国也是后来而居上者。一些国家明确了禁止燃油汽车的时间表,中国也在2020年11月发布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纯电动汽车在新车市场的销售要占到20%左右,2035年成为新车市场的主流。目前,我国纯电动汽车的保有量稳居世界第一,纯电动公共汽车占全球比例高达98.2%(见图4、图5),其中,深圳市公共交通车辆已全部实现电动化。
资料来源:IRENA(2021a)。
资料来源:IRENA(2021b)。
传统化石能源能源密度高,经济性能好,运输储存便捷,可以按需求随时调节。相对来说,风、光乃至于水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在常规技术视角下,不具备竞争优势。技术进步已经使得新能源具有成本竞争优势,但是其储运和调节柔性程度,仍然具有一定的劣势。正因如此,目前业内对化石能源彻底退出以实现碳中和存在一定的疑虑,认为仍需要大量的化石能源来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给。例如对于零碳的间歇性能源,在储能技术没有革命性突破的情况下,电网的消纳能力比较有限,不可能完全放弃火电。我们要相信技术进步,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问题已经或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德国规划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中的占比达到35%。相对于2000年只有6.3%、 2010年17%的占比来说,这一目标不可谓不高。但实际上,201942%202046%显然,目前德国的电力系统仍然是稳定的、安全的。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并网的风光电力,只有10%左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1)。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选项,就是终端治理。煤电排放的二氧化碳可以采用CCS技术,如同火电机组脱硫、脱硝一样,将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加以捕集、浓缩,然后找到合适的地质结构,永久埋存于地下。所谓CCS技术,最初是石油开采过程中为了提升采油率,将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加以捕集,注入到油田驱油。该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IPCC于2005年专门发布了一个特别报告,评估了这一技术的潜力和可行性,并在随后的第四、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将CCS作为一个技术选项,但并没有就成本问题深入解析。《巴黎协定》签署后,中国系统梳理了各类CCS 技术,涉及深部咸水层封存、二氧化碳驱油、二氧化碳驱煤层气等。截至2019年,中国共开展了9个捕集示范项目、12个地质利用与封存项目,所有CCS项目的累积封存量约为200万吨CO2。在煤电成本已经不敌可再生发电成本的情况下,煤电加CCS,增加的成本不仅包括捕集成本,还有运输与封存成本。低浓度捕集成本为300~900 元/ 吨CO2,罐车运输成本约为0.9~1.4元/吨·公里。原油价格在70美元/桶的水平,大略可以平衡CCS 驱油封存成本。所捕集和封存的二氧化碳,具有零效用,直接或间接使用价值有限或为零。不仅如此,封存后的二氧化碳还存在逸出风险,必须持续监测。况且,捕集的比例也比较低,不可能100%捕集。因此,总体上来看,CCS技术不仅是理念问题,也缺乏市场竞争力(蔡博峰等,2020)。
如前文所述,森林碳是气候中性碳,通过造林和森林培育、生态系统保护,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维系一定量的碳汇,中和部分化石能源碳排放。但限于我国水资源短缺、戈壁荒滩和雪域高原不适于植树造林的实际情况,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森林碳汇的空间比较有限。根据全国森林普查汇总资料,2018年,全国森林面积为22044.62万公顷,森林蓄积为175.6亿M3,全国森林植被总生物量为188.02亿吨,总碳储量为91.86亿吨,每年固碳量为4.34亿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没有水,就没有碳汇(山仑,2013),没有生物质能。我国干旱半干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2.5%,其中,干旱区占30.8%(280万平方公里)、半干旱区占21.7%(213万平方公里),碳汇生产量也不可能高。2010年前后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在我国水热条件比较好的西南地区如四川、云南开展的一些森林碳汇项目(吕植等,2014),核算时间在20到30年,折算下来每年每公顷碳汇产出量在10吨左右。如此算来,每平方公里的碳汇量每年也只有1000吨二氧化碳。
光伏电力是必然的选项,但由于光伏铺设对土地利用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可以是戈壁荒滩,也可以是屋顶空地,但不宜占用农地、林地,以及自然生态良好的山地。净零碳需要“大干快上”,但不能“得不偿失”。例如,浙江、贵州的一些作为碳中和典型和经验介绍的个案,均是将一片山地的森林毁灭后,连片安装光伏发电设施。光伏必须要阳光,森林也要依靠太阳辐射实现光合作用。在森林植被较好的南方山地建设光伏电站,不仅灭失碳汇,而且会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生物多样性。
资料来源:吕植等(2014)。
颠覆性的技术革命是碳中和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社会发展和运行方式已然高碳,碳中和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通过体制性的软技术变革,可以有效压缩需求,使得许多化石能源消费成为不必要,能源需求大幅减少,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区域空间规划,工业文明的理念是工业化大生产,远距离运输,从而获取规模和聚集效应(潘家华,2019a)。但自然的风光和水是普惠性的,大略均衡。在工业文明理念下,城市无序、无限扩张,能源不够,特高压远距离输送电力;水资源不够,可以从数百公里乃至千公里外远距离调水;水果蔬菜粮食也都是通过规模化生产,远距离运输、储存、保鲜。所有这些,均需要能源作为动力来完成。改变理念的认知革命,实现从垄断聚集到扁平均衡,就可以大幅压缩能源总量的刚性需求,事半功倍地推进碳中和。从根本上消除高碳锁定,就近就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减少乃至于消除高强度、高频次的高耗能需求,从依赖高碳化石能源的规模扩张、空间集聚,转向适应零碳可再生能源的适度规模、空间均衡格局。空间上均衡、均质,与自然和谐的资源配置,减少需求总量,就近获取零碳能源服务。
工业文明的城市空间设计,强调城市功能分区,职住分离,产城割裂。城市空间的扁平化与职住一体、产城融合,可以减少碳存量与运行需求。例如低碳交通,如果职住一体的话,就不需要交通,自然也就没有碳需求,实现零碳交通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强调等级梯次,在一个行政区域内,按照“核—中心—副中心—次中心—节点”的等级分异配置资源。如果要拥有优质资源,就得到“核”或“中心”、“副中心”。如果改变理念,实现特色—互补的扁平均衡均质,就近获取城市公共服务,许多高碳的能源需求,就成为不必要了。
我国人口数量多,土地资源有限,因而在城市建设中,一方面为了城市形象,普遍建设超高层建筑,一些地标楼宇更是动辄300米、500米,甚至更高。殊不知,建筑楼层过高,必然高碳。高碳一旦锁定,实现低碳的难度就增大,碳中和空间变小。这是因为楼层越高,材料耗用就必然越多,维护维修就越难,运行费用必然越高,火灾风险加大,而且高楼内人员密度高,疏散慢,楼宇更新难度大,地质灾害影响大。2001年美国纽约国际贸易双子塔遭受恐怖袭击,灾难性破坏的碳含义是不言而喻的。迪拜的哈利法塔是工业文明的技术奇迹,但从碳锁定视角看,显然是高碳的典范。该楼宇高达828米,建筑层数多达162层,连同地下共有169层,游泳池位居第76层。清洁工们为了开幕庆典,耗时3个月清洗大楼表面。整个建筑共设57部电梯,包括时速64公里的世界最快电梯。所有这些,每一项都是高能耗、高碳排放。即使是光伏发电,也需要大面积远距离提供。
通过体制性的软技术变革,可以有效维护、延伸、放大碳资产的社会效用。一些制度刚性的社会性变革,可以保全社会碳资产。例如小产权房、自然保护地内的建筑(在划定以前就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征占地上建筑等。这些年来,许多地区严格执法,炸毁、拆除大量小产权房、违建房。法律上,这些违法建筑应该清理,但从碳资产视角,这些都是凝聚大量碳的社会资产。我们需要惩戒的是违法的人,需要处罚的是非法获取的利益,而不应该是社会需要的碳资产。因此,宜在制度层面减少或避免社会碳存量资产的损毁,在管理/文化因素层面,也有许多需要变革的地方,比如严格产品质量,提升碳效用。例如,一栋建筑是30年寿命、60年寿命,还是120年寿命,碳足迹没有本质的差异,但碳效用却差了数倍;一台发动机,碳足迹几乎无差异,但碳效用差距却可能特别大。
一些机制、政策性因素,例如循环经济,也可以保全碳资产,提升碳效用。对于“二手”或“旧货”,在机制、政策、文化和心理上,均存在“厚古薄今”“喜新厌旧”的市场理念。“厚古薄今”是指对于当前仍有使用价值,的各种“二手货”视而不见;“喜新厌旧”则是指对于仍然具有大量使用价值、但不再时髦的产品废置弃之。从碳效用视角,需要在机制、政策上,让循环经济运转起来。许多废弃物,多为机构或个人消费者因无地存放而扫地出门,多为半新半旧或纯然新购未开封产品,质量性能仍可满足正常消费需求,可直接进入市场交易或经产品标准核认后进入市场,释放碳效用。从政策引导层面,需要推动从“城市矿山”到“无废城市”。“城市矿山”是指碳资产灭失,需要高碳再生形成新的碳资产,而“无废城市”具有再利用导向,使碳资产延续。
碳中和,需要政策引导,更需要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型。
第一,在政策层面,碳定价显然有助于提升零碳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有助于激励低碳消费。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市场交易,具有碳价的发现功能。在碳交易的初期,如果交易成本足够低,碳交易有利于日渐减少的碳排放额度的效率配置。但实现碳交易,需要专署登记、专项交易。由于碳的无形特征,企业的核算、核查需要投入,第三方认证核查也需要成本,而且,鉴于气候灾性碳的市场恶品(bads)属性,碳市场不可能做大做强,不可能持续,从长远看,没有可预期的未来。在碳中和实现时,碳市场也将消亡。相对说来,碳税交易成本低,可以产生双重红利,提升气候灾性碳能源的供给成本,提升气候中性碳和零碳能源的市场竞争优势,从而加速气候灾性碳的市场退出。
第二,可再生能源要实现协调互补。由于化石能源的集中性和高密度,规模化大生产,经济回报高。可再生能源占用空间大,难以规模化大生产,能源密度相对较低,这就要求协同互补。首先,多能互补,风、光、水、生物质能、储能技术协同互补。其次,也需要区域协同,西南水能、西北风光、东部离岸风电,区域协同互补。城市人口密集,经济活力强,能源需求大,难以在城市区域内实现碳中和,而乡村空间广阔,可再生能源生产潜力大,除了满足自身需要,还可以外送。因此,城乡协同也是必要的。颠覆性能源技术的应用,并不是完全否定能效技术,相反,需要能效技术和能源替代协同互补。即使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温升幅度仍将达到1.5℃,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均需要适应变化了的气候,降低气候风险。因而,碳中和还要与气候适应协同互补。
第三,碳中和正在催生发展范式的革命性转型。碳中和阶段,能源生产与消费实现一体化,零碳经济单元自给自足,而不是传统的供求分离,通过市场实现均衡。传统的规模化大生产(规模效益)与自然容量刚性的矛盾,成就了低碳、零碳的就近、分散空间资源配置,促使从空间聚集(聚集效应)向空间均衡的转型。城市空间的功能分区与功能融合方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职住一体、产城融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贴现率、高折旧率,形成财富周期的加速再生增值(高贴现率)。但这样会加速碳存量资产的贬值,需要实现碳资产存量的持久保值(近零贴现率)。城市形态高碳技术的“高”“大”“尚”与基于自然和谐共生的解决方案,从排他性、占有性产权转向“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共享型经济,均是发展范式转型的雏形(潘家华,2019b)。
第四,实现碳中和,既要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也要系统性的社会变革。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颠覆性技术革命,是碳中和的必要条件;系统性的社会变革,量级水平压缩刚性需求,放大碳资产效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碳中和的充分条件。在强调零碳能源转型的同时,提速社会扁平化进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碳中和的必然选择。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9UoESEcGJjX2zSP2Or5A
(转“ ”)
http://www.chinacem.net/info.asp?id=2769
原创文章,作者:化工管理,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chinacem.net/924.html